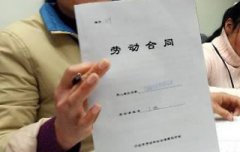当一个儿子拍下快递厂里的妈妈

过去几年,他开启了一个名为《快递》的摄影项目,用大画幅相机给400多名快递工作者拍摄肖像照。镜头里,他们的表情总是有些严肃,脸上的沟壑很深,手糙糙的,背厚厚的,有一种油画般的庄重感。他说,他希望拍摄的是,一个人就像一座雕塑,伫立在自己的工作空间。2024年,这组作品入围了徕卡·奥斯卡·巴纳克摄影奖主竞赛单元,牛童也成为自1979年以来第四位获得提名的中国摄影师。
这是他的毕业作品,想法缘起于母亲。2020年底,牛童的母亲进入南京一家快递转运中心,成为一名分拣员。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,他跟随母亲进入工厂,意外走进了快递工人的生活。
在快递厂里,他见到一代人的缩影:他们大多来自苏北、皖北和西北地区,跟随打工潮来到江苏,辗转于各个工厂之间。他听他们聊曾经的梦想,去到他们的家乡,看见他们的来处,也见到他们如何在城市中打拼,又如何努力挣得有限的生存空间。
二十多年里,牛童从出生并成长的南京郊区,走向西安、北京,通过读书改变了自身的命运。很长时间里,他一直逃避自己的过去,他说,如果不是因为拍摄母亲的工作,他可能也会变成曾经向往的精英模样。是《快递》这个项目让他有了回望的勇气,「我就是这样的人,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。」
拍摄进行了5年,仍在继续。5年里,他经历了母亲从患癌到去世的过程。这也是二十多年以来他和母亲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。他一点点捡拾起母亲的故事,重新理解了一个单身妈妈的不易:很多年前,母亲一个人从安徽宿州来到南京打工,她去过文具厂、医疗机械厂,做过保险,代理过酒水,摆过摊、开过小超市。她肆意过,也失意过。今年年初,母亲去世。按照母亲的遗愿,他把骨灰撒进长江,顺着江水漂向远方。
他向我们讲述了过去几年的拍摄经历,照片背后的故事,还有这个过程中他和母亲的点滴相处。能明显感受到,牛童还没有从失去母亲的哀伤中走出来。几乎每一个问题,他的讲述总会落回到母亲身上。他说,他是一个妈妈带大的孩子,也会带着妈妈的眼睛生活下去。
小学的时候,我父母就离婚了,我是妈妈带大的孩子。记忆里,她一直在换工作。2011年下岗前,她在一家文具厂,经常要搬重物,有一回工作的时候,腰受伤了,后来她被裁员,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她腰不好。在那之后,她就辗转各个地方打零工,去过医疗机械厂,做过保险,代理过酒水,也自己摆过摊、开过小超市。
但这些事我当时都没概念。我记得初中的时候,班主任统计班上每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月收入,我答不上来,回去问我妈,她给我说的意思就是,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。没有别的话。后来我离开南京,去西安上大学,离家一千多公里,像端午节这种三天的假根本回不去。我本科学的是影视制作,从大三开始就会去一些剧组打工,赚生活费,有时候寒暑假为了省钱,也不回家。
所以很长时间里,我跟家里的关系一直挺线年,我读研一,有天我妈给我打电话,说她去了极兔速递做分拣工作。听到这儿,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那时所有普快基本都是爆仓的状态,我妈的腰和手因为之前的工作受过伤,我不想让她再做那么重的体力活了。考完试回到家,我们因为这个事吵了一架,吵完我又有点羞愧,担心话说是不是说重了,所以主动提出想去她的工厂看一看。
第一次去是接她下班。厂子在城市的一个夹角处,左边是化工厂,右边远一点的是回迁房,两侧都灯火通明的,只有这块没有路灯,很黑,盖的也是瓦棚房,越往里走越觉得陌生,你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这座城市没什么关联。
2020年12月,牛童晚上接母亲下班,一片从远处延伸而来的积水,倒映着城市的光景。
因为是晚班,最后一批货也都拉完了,就几个人在那收拾。尤其那晚下了雨,在一个黑压压的场地里,只有水坑是亮的,倒映着城市远处的夜景,那种感觉,有点梦幻,又有点魔幻。
我妈看到我,招呼我过去。我跟她说,这个地方拍照很好看,她可能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,站在旁边等我拍完回家。我们的相处一直都是这样,她不会因为我来接她下班特别惊喜,也不会因为我们吵架特别难过。她十几岁就从村里出来打工了,习惯了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。
后来我骑着电瓶车载她回家,我俩都穿着雨披,我想起小时候在雨棚里,当时可能是无聊,又有点好奇,挺犯贱的,把脚伸到车轮轴里,脚趾盖整个被掀翻。我妈本来要去上班,最后只能带我去医院包扎。但她没责怪我,只是问我疼不疼。那天我妈坐在车后座,我就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。
下一次跟我妈进工厂,那个画面极其夸张。快递厂的白天和晚上是完全不同的。卡车开进来,货物全部卸下来,你就感觉人都被埋到那些货里。没有人说得清一卡车到底有多少件货,根本数不过来,我妈只知道这一天,她要干1500票到2500票,在快递厂,计量单位不是货物数量,而是车型,这一趟是一辆四米二的车,下一辆可能是十几米的车。
只要忙过那个时间,又会有一段非常真空的时间。上午的车已经卸完,货也都分拣完、被拉走了,人都散去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,人去楼空或者怎么样,都没办法形容我在现场的感受。后来有些老师得知我要拍摄这个主题,希望我能拍出那种冷峻的、机械化的画面,但那都不是我当时的主要体验,我的体验是,人忽然不见了,他们到底去哪里了?
但当时对于拍摄我妈的工作,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。后来回到学校,我还是老想着我妈的事儿。到了双十一,我会很担心,不知道她的工作忙不忙,累不累。就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,不要老是关心自己的状态,至少去看看我妈在干什么。
进厂之前,我对快递行业的了解很少。当时以为,分拣这个工作可能跟我妈之前在文具厂做女工的状态差不多,不断地装货卸货,把东西放到该放的位置。真正开始干的时候,我发现它跟我想的还是不一样。
为了保证速度,人会卡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上。一只手拿着扫码枪,另一只手往后扔快递,动作就跟兰州拉面的机器人一模一样,只不过手是反着来的。一趟车的货物,基本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干完,干不到一会儿,整个肩膀到手真的会巨酸无比。
一开始,我还没正式拍,只是跟大家聊天。普快讲究的是量大,有时候,工人之间也会吐槽。遇到大件,同组的人可能会顺带帮一下,这时候大家会说,谁会买这么大一个东西啊;拎到沉的东西就说,这一定是一个养宠物的人买的。我也受过几次伤,其实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,就莫名其妙地身上被划了一些伤口。
他们知道我是因为妈妈才来做快递,对我很好奇。当时我跟一个叔叔一起开车送货,他会跟我讲我妈的事情,我也会问问他家里的事。碰到有孩子的,他们会更好奇,有一个师傅的女儿马上要高考填志愿了,女儿想学摄影,但他觉得摄影费用特别高,问我每年要花多少钱,我跟他说,我大三开始生活完全可以自理。就这样子我们交流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但在厂里的那一个月,我始终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。一方面我确实太年轻了,我就20多岁,大家至少是三四十的年纪,后来当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研究生,就更奇怪了,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?在大家的眼中,我是因为体贴妈妈才进场帮忙,不会把我视为一个同辈。
也是在这个过程中,我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,你到底想要拍什么,或者说这个项目的意义在哪里?
我发现自己最关心就是他们的个人故事。听到他们的口音,我会好奇他们从哪里来,慢慢问了更多之后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同乡。还有一些阿姨来这里,是为了能回去给孩子做顿饭,因为快递厂中午是可以回去的。
我也会想到小时候。小学的时候,我妈上的是夜班,经常半夜醒来,发现家里没人,会有很强的不安全感,不知道漫长的夜晚要怎么过。当时电视上老放TVB的鬼片,还是挺吓人的,在那种状态里,我一直都不理解,为什么妈妈要上夜班。
当成为一个旁观者,看到这些阿姨的时候,我忽然就明白了,我妈上夜班就是为了能够白天照顾我,晚上走之前,还能给我做好饭,这样我放学回来,加热一下就能吃。我也会想起她以前上班的时候总是戴着耳塞,因为工厂晚上的噪音很大。
最开始拍摄,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阿姨。那天晚上,我们原本是打算去她家拍照,但过去的路上,她和我讲起,以前她是送外卖的,有一年冬天,她在一个老小区配送,路灯很暗,不小心踩空掉进了景观池,棉袄全湿了,但手上还有单子要送,只有送完才能回家换衣服。
听起来可能就几句话,她就把事情讲完了,但是那几句话组成的事情,我们脑子里都有画面。后来我问她,你跟家里人是怎么说的?她说,过了一段时间她给儿子打了个电话,没说别的,就是问了他最近学习怎么样。
可能就是这种隐忍,让我想起了我妈,她们都在外面漂泊,一直在服务别人,从来没考虑过自己。包括她讲起受伤这件事,听上去好像很私人,其实受到伤害对他们来说是很「正常」的事情,但凡你跟他们多聊一会儿,分拣员们都很愿意打开,因为在生活里,很少有人愿意听他们讲。
那天也是一个下雨天,我对南京这座城市最深的感受就是雨。后来我们决定就在小区楼下拍,站在一个看起来又像家又像路的地方。我们往往会忽略掉楼梯、道路这些过渡的空间,它们不像家或者工厂,可能不承担具体的意义,但代表了一种不断移动的感受,我希望能够把这种感受拍摄进去。
刚开始拍摄,我用的是小相机。当时想法很简单,快递是关于速度的工作,拿着小型相机可以捕捉这些瞬间。但是拍着拍着,总有一种感,或者猎奇感,我只是获得了他们工作过程中的一个截面,他们也会反馈,自己在镜头里并不好看,或者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有点木讷。
后来选择用大画幅,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特别笨重,操作也很麻烦,你跟拍摄对象需要进行长久的沟通,才能完成照片。最开始沟通拍摄,大家都会很谨慎,担心自己的工作是不是不体面,或者觉得我有别的目的。
很多人也会很害羞,尤其是旁边人一起哄,他们就会说「我不上相,不拍不拍」,或者「我不好看,你去拍TA」。但我会跟他们说,「我觉得你很特别,哪里特别」,对方就会建立起信心。
对城市中产或者白领来说,摄影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但对他们来说,当一个免费的、服务性的东西进入到生活里的时候,第一反应是不习惯。所以沟通有时候会变成送红包一样,我不能收,我不能收,需要反复推拉一阵子。
在这个过程中,交流很自然地发生了,有些人会问我,这东西还能拍不?也会问现在还有胶片吗?他们会开始关心摄影的问题。有些人可能会问你的工作和生活,比如靠什么赚钱,我就说主要靠拍短剧、拍短视频。所以拍摄的过程也变成对方了解我的过程。对我来说,这也是一种方法,至少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、互相知情的状态中拍摄的。他们对我会有更多的信任。
在快递厂待了一个月,我就回学校了。那段时间,我并不清楚这个项目会不会持续下去。后来因为我妈妈患癌,我休学回南京陪她,那是我人生中我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,也是《快递》这个项目的转折点。
2022年5月,有一天,我在图书馆自习,接到我妈的电话,一开始就是聊聊日常,后来她跟我说,她生病了,查出了肿瘤。已经是四期了,但她没说。我问她,有没有转移,她才犹犹豫豫地说,肝上有一点点,医生说能切。
在医院陪护的那段日子,虽然很辛苦,但就像我之前在快递厂不断问自己的那样,为什么别人能坚持下来,你坚持不下来?当时碰上疫情最严重的时候,基本上两个月我都没有离开过病区。我也发现,医院是个很现实的地方,你真的能见到一些中年男性照护到一半,就跑掉了,能坚持下来的,大多是女性。
我妈是先做化疗,把肿瘤控制住之后,才做的手术。我记得很清楚,那场大手术持续了6个小时,后来我拿了相机去拍了切下来的肿瘤物,我的手很抖,拍完之后,心里觉得,这个事儿总算要告一段落了。
做完手术,封控结束,我跟我妈都阳了,休养了一段时间,我妈跟我说,她想回老家看一看。其实老家早就没人了,外婆在我初中的时候就走了。回去的时候,我妈也很失落,她记得这边有很多杨树,现在没了;当年她走出村子要拐很多弯,现在桥也修好了,村子里以前认识的人都不在了,外公外婆的房子早就被推掉了,有一种家无处安放的感觉。
也是在陪我妈回乡的过程里,我对《快递》这个项目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之前我更多拍摄的是快递员的单人肖像,那个时候我想要关注他们背后的故事,我想知道,他们从哪里来,又为什么来到城市。我想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,他们和土地的关系,他们和家庭的关系。
2023年春节,我联系以前厂子里的人,想跟他们一起回老家看看。我去过一对老夫妻的家里,他们是安徽人。最早儿子在城里做快递,后来失业,家里压力很大,老夫妻才进城做分拣。因为口音太重,他们没办法跟别人沟通,每天收工就回到一间门卫室大小的宿舍。
但进到他们老家的房子里,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。印象最深的是墙上那幅泰山的画,旁边还挂着梅兰竹菊,特别有乡村里中堂的感觉,你也能从里面看到很传统的文化底色,包括联想到他们在城里生活的不习惯,为什么还是想要回到老家。
来南京这边打工的,主要是苏北、皖北和河南一些地区的人。看上去是三个省,离得都很近,文化的认同感也很相似。记得有一次我在江苏泗洪那边拍摄,有一个安徽那边的拍摄对象打电话,问我什么时候去,我说我在泗洪,他让我把定位发给他,他一看就说,近得很,开着五菱宏光就过来了,把我从这头拉到那头。
还有一个小哥,原本是去另一个地方拍摄。但他过来接我,路上聊的时候,他一直在提一座山,那是他们附近七八个村子唯一的一座山,他小时候经常会去爬。后来我提议去那里拍。到了那里,其实都不算是一座山,就是一个山坡,背面那块是石料厂的开发工地。他站到山头和我讲,小时候,他会爬上来,眺望不同人家的村子,山的底下是坟堆、墓碑、松树,然后是水泥路,再往前就是柏油路。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拍摄的机会,他可能也不会再回来看一眼了。
对于那些在村子里的留守儿童,虽然他们和父母是有感情的,但始终有隔阂。这也是很现实的事情,为了讨生活,必然有一部分会被牺牲掉。可能他们在这个阶段无法理解,必须得过了很久以后才能明白,当然到了很久以后,这种理解会形成一种陌生感。所以回乡拍摄的过程里,如果可以的话,我会给全家人拍一张全家福。
我还拍过那对老夫妻的儿子和他的儿子。之前他们进城要坐轮渡,他带着我去了那个渡口,早已经荒废了,但标识牌还在,这边指向宿迁,那边指向徐州。我让他们一个站在船上,一个站在船下。他和他儿子长得是真像,都胖胖的。他跟我介绍,现在村子不走轮渡了,是因为修了好几座桥,这样劳动力就可以往江苏跑了,留在村里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。
返乡拍摄的过程中,我一直在思考代际的问题,这张父子的照片让我触动很大的原因,不仅是父子长得很像,他们的故事也很像。
大家为什么来到城市?通俗来讲就是钱。我妈跟我说过,小时候她想读书,但家里有好几个孩子,她最小,没钱,家人觉得女孩要嫁人,识字没用,小学她就辍学了,在家帮忙掰玉米。当时她的手都没发育好,掰一会儿,很痛,她就哭,不想掰。到十三四岁,有一次她闹脾气顶撞外公,外公打她,她一气之下偷偷收拾东西,准备离家出走。外婆跟她关系特别好,两个人晚上在房里抹眼泪。最后是外婆把她送到了村口。她坐上中巴车,就来到了南京打工。
那个年代有机会,她在城里找到工作,买下房子,但她一直还是有遗憾。我记得初中的时候,我们住的地方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很近,这个学校毕飞宇很出名,我妈立马给我买了毕飞宇的《推拿》。
包括我现在成为一名老师,很大原因是想让我妈能安心。尤其是她生病后,一直希望我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,虽然我并不觉得老师是我一辈子的规划,但我也愿意为了她,看起来安心与稳定。后来,在学生身上,我能看到曾经的自己,学生给我也带来了许多疗愈。
我对学生说过最多的话,大概是,需要多走出校园,做学生也不必太「乖」,找到自己的目标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。
做完这个项目,很多人都觉得和他们想的不一样。大家希望看到那种宏大的、结构性的东西,那些别人拍不出来的画面,但我的照片都是日常的。记得2023年毕业展的时候,很多人看完,最大的感触就是,这不是拿手机就能拍吗?我说,我是拿大画幅相机拍的,他们觉得这是浪费器材。
如果是以前,我会很在意这些评价。拍摄《快递》前,我也像很多艺术生一样,希望自己能在艺术上有一些成绩,拍出别人拍不出的东西。有过一段时间,说起《快递》这个项目,我都会有点羞耻。怎么形容呢,就像是你给一个陌生人去展现自己最本质的生活。而这些生活,我过去一直是主动逃避的。
我从小生活在城乡接合部。家住在燕子矶,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开发区,但在当时两边都是巨大的化工厂,后面就是农田、火车轨道和零星的村子。上下学的时候,化工厂飘下来的白色粉尘会将整条路染白,从草木、石头到屋顶,全部雪一样的白。过一段时间,白色会变成灰色。生活环境也挺乱的。小学的时候,我就跟着一些邻居去网吧打游戏,从白天一直打到晚上。有一次被我妈发现,狠狠打了我一顿,拿织毛线的针戳我,让我跪在键盘上反思。后来带我去网吧的很多朋友初中就辍学了,有些甚至进了管制类的学校,再也没有见过。
从小学到初中,我的体验始终是介于混混和学生之间的状态,学习不是很好,混也没真的去混。高中上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校,没太多人能靠文化成绩考上一本。我一直很喜欢画画,也喜欢写点东西。后来通过画画考上了西安艺术学院。当时油画和国画是主流方向,但是一个画家要想出来的时间成本很高,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,所以我就想学一门手艺活,报了影视制作专业。当时的想法很实际,实在不行,回家还能开个影楼。
但上了大学之后,我才发现,影视制作不是普通人的游戏。大三那年,我帮一个朋友做毕业创作,大家算上人情,攒了二三十万拍一个片子,不是一个小数目了。我们的片子确实入围了一些奖项,但当时很多比拼的并不是对生活细节的观察,而是比拼观念,比拼技术,30万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,我们后面没办法再掏10万做更多的事情,最后也挺打击的。后来毕业选择了纪录片方向,研究生的时候,就转向了图片摄影,我觉得如何理解现实是急需解决的事情。
成长过程中,我最大的困惑也好,自卑也好,就是我的身份。我虽然生在南京,长在南京,但身份证是安徽的。上了小学之后,有些老师会问你父母在哪里,有些孩子会受到父母影响,歧视你的出生地。
大学我上的又是艺术学院,朋友们从商从政,都有不错的支持。在这样一个成长环境里,他们从小的心思就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,遇到最不顺心的事情就是被人骂了两句。我后来也在宿舍深夜相互交流了通宵,我们都感慨对方的出身和底蕴,很多东西是缘分也是造化,怎么找到自己的课题并解决它,显得异常重要。
回头来看,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在快递厂工作,我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群体,我可能也会慢慢往我曾经向往的精英的样子去发展。但是因为《快递》这个项目,也因为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太多事情,现在说起这些,我会轻松一点,因为这个作品让我确定了,我就是这样的人,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。
写解释词的时候,我只能讲述我的个人经验和感受。虽然看起来我的工作量很大,但最终完成的不过是别人生命里的一个切片。
中国的物流和快递行业应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,在里面工作的人们,他们曾也处于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。离开中小县城流动进大城市,这种迁徙与现代化、梦想有关。
我拍摄的快递行业主要是江苏、安徽地区,这里面的快递员大多来自于苏北、皖北和西北地区,他们织起了一片同乡网络。他们期望窥见外界的精彩,在时间流逝下老去,也将这种梦想寄托于后辈身上。
从2020年底开始,我与快递人员沟通,走进他们家中,走回生地。以逆城市化的方式追溯,访谈、收集现成品以及拍摄下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的场所,暂居的屋檐下,病痛以及生地。摄影赋予我走进现实的勇气,采用大画幅的方式进行庄重的拍摄,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。
这组作品能够入围徕卡摄影奖,我蛮惊讶的。那段时间,我的状态挺不好的,2023年年中,我妈做完第二次手术后,肝脏切掉了一半,还是没有控制住,后来化疗的效果越来越不好。她住院的日子,我又开始失眠,小时候失眠是因为醒来找不到她,现在失眠是因为恐惧,我害怕妈妈会离开我。
收到邮件的时候,我才意识到我之前投过奖。我不敢相信,立马私信我的图片编辑,我反复问她,「我是不是入围了这个奖项」,她说,「是的,你可以很自豪地说你获得了这个奖项。」
后来邮件沟通,组委会有一句话很鼓励我——你完全可以为你的成绩而感到自豪,因为你是被一些影响摄影界的人选中的。
原本我打算带着我妈一起去德国领奖,但那时她的身体很虚弱了,要坐17个小时的飞机,她不想那么折腾,最后我自己去了。到了现场,我拍下一张妈妈的展映照片,跟她说,你看,连德国人都在看你的照片。她可能也不懂,在她的概念里,只知道儿子出国了。
我把一些照片寄给了拍摄对象。叔叔阿姨并不知道我拿奖到底有什么用,但电视台去采访,他们会高兴地介绍,夸我有出息了。这就是他们表达情感的方法。但说到底,我做的这件事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。可能最大的改变就是现在快递厂越来越难拍了,基本都有摄像头了。
看到照片,他们不会想很多。有人可能会说,这不是那谁吗?或者指着照片说,拍得还挺帅,各种调侃的话都有。也有些人不干快递了,看到的时候就说,原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的啊,然后跟你回忆一些往事。
印象比较深的,是有一个大爷说,「我终于有一张像样的照片了。」如果你看过快递员的照,通常就是拿一个手机,不太会注意炫光、构图,特别是晚上,路灯或者工厂的灯光呲下来,滤镜很重,画质也很差,常常拍得五迷三道的。但因为我用的是大画幅相机,人是很板正地出现在你的眼前,你能很清楚地看到脸上的细节。
生活中,你可能不会那么长久地凝视这些快递员,但是当他们的肖像出现在你的面前,你会不自觉地被他们吸引,在这过程里,你可能也会意识到,快递员只是ta的一个身份,ta首先是一个你身边的人。布展的时候,我也会希望我拍摄的对象和观众之间是平等的,所以我会把照片挂得高一点点,让人带点仰视地去看他们。作为摄影师,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。
获奖之后,也有人羡慕我的成绩。我会跟他们说,这个选题其实谁都能拍,只不过对我来说,它多了一层意义,关于我的母亲和我的来处。这是我人生经验里的东西,相比其他人,我失去了一些,也获得了一些。教学的时候,我也会和我的学生说,当你已经站在一道窄门前,你还是可以通过创作或者记录的方式留下那种感受。
从2020年底到今年,妈妈一直是《快递》这个项目的交合点。但在我拍摄的400多张照片中,妈妈的照片只有几张。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件事,摄影代表的是过去和消逝,甚至是一种死亡。当我把镜头对准妈妈的时候,我是知道这个行为背后的意义的。我知道我妈会离开我,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这样的设定。
所以每次拍摄妈妈,我的表情总是很严肃,我妈也会很严肃。其中一张,她站在她的房间里,后面是黑的,只有一束阳光照进来,打到她脸上。如果看得足够仔细的话,你可以在妈妈的眼睛里看到我。
牛童想给妈妈拍摄一张「标准照」,虽然她看起来有些疲惫,但她很爱漂亮,热爱生活。
拍摄的时候,我思考了很多,包括死亡,母性等等。我妈还问过我,你怎么都不让我笑一下。摄影就是这样,我们会以对方为镜子,如果摄影师不笑,你也不笑。后来,这张照片成了我妈妈的大相。
我妈妈是今年年初去世的。按照她的遗愿,我们把她的骨灰撒进长江,顺着江水飘走。直到今天,有空我就会去江边坐一坐,带两块江边的石头回家,留一块放在桌上。只要路过南京,我也会回家,把那些高铁票放到家里,我想给妈妈看一看,告诉她,自己最近去哪里了。
很多事情都是后来我才明白的。有过一段时间,我不敢打开妈妈的手机,但有一天阴差阳错,我忽然很好奇我在上学的时候,我母亲在干什么。打开她的朋友圈,我发现她其实很孤独,她发了很多,发了很多生活的照片,讲了很多话,但这些内容她都把我屏蔽了。
2018年的时候,她发过一段小视频,画面里,她开着电瓶车,背景声音里忽然响起一句:你已经偏离航道。我才知道,她还送过外卖。我还翻到她相册里的一张截屏,是有一年的母亲节,凌晨三点,我刚从剧组回去,给我妈转了红包,她给我发了一个三秒的语音,我看她这么晚没睡,就跟她说,早点睡。这件事我其实已经忘了,但看到截屏上有地图方位的标志,我才反应过来,那天晚上她应该也是在送外卖。
所以为什么我会对那个穿着雨披的阿姨印象深刻,就是因为我在那张照片上看到了我妈妈。
现在回想,虽然成长过程中我妈跟我的交流很少,但是她真的很关心我。她其实上过白班,但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,好几次班主任把她从工厂喊过来,一天都白干了,但她没有责怪过我。还有一次,她要上夜班,留了一个西瓜给我。我是左撇子,切西瓜的时候切到了右手,差点见到骨头,我妈又从工厂跑回来送我去医院。所以后来,她才会找那些可以三班倒的工作。从小到大,她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吼过我,学校开家长会,有些家长开完会直接向孩子发火,我妈一次也没有。
也是在回忆一件件小事的过程里,我慢慢发现,我一直在带着母亲的眼睛生活。我记得高考语文的作文题,大家都在写议论文,只有我写了一篇小说,写的是一个家在水乡的小伙子回去参加一场葬礼。故事很简单,讲的他离开水乡的原因以及回乡路上的见闻。这个故事的原型,就是初中时我妈带我回去参加外婆的葬礼。所以从故事的一开头,我就是带着妈妈的视角在写那个小伙子。
拍摄《快递》的时候,看到一些场景,我会不自觉地想起妈妈。比如有个叔叔说他之前住在这里,后来拆迁了,原本这边住的是谁家,那边是他的同乡,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南京。我就会想,这个经历怎么跟我妈妈的那么像?只不过我妈好像更厉害,她在这儿买了一个小房子,让我有了一个居所。
我以前总觉得,一个人回忆另一个人,总是关于那些重大的事情。但这半年来,我发现更多留存在我记忆里的,是一些日常的小事,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我家窗外有一棵枇杷树。生病前,妈妈每年都会摘下一箱寄给我。其实吃起来没什么味道,剥的过程又很麻烦,核又大,肉又少。大学时候,我分给室友吃,他们的评价跟我差不多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坚持摘。
妈妈生病后,她就没再主动去摘过那些枇杷。前段时间有一天,我回家发现一只鸟站到了枇杷树上,一直在叫,天刚蒙蒙亮,你能闻到早晨那种清冷的味道,可能鸟儿也有同感吧。我就开始想象,我不在家的那些年,妈妈是怎么站到墙头,摘下这些枇杷的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